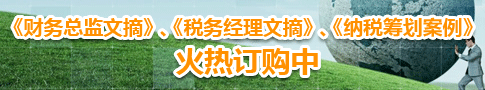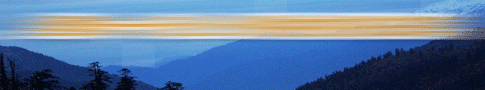自2012年1月4日一审第三次开庭之后,历经数次延期,盐湖集团股权案仍未有结果。迄今为止,既未再次开庭,也未宣判。
在距离该案最后一次开庭一年零七个月之后,证券时报记者获得了一份该案当时的庭审记录,还原了盐湖股权案中代持公司的股权转让造假过程。
工商变更谁在造假?
盐湖集团股权案涉及的焦点是兴云信100%股权的转让过程造假。
2011年9月,昆明市检察院向昆明市中级法院对张克强等人提起公诉,指控其从2001年起精心设局,并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冒用兴云信的国企身份,参与盐湖集团增资扩股。
增资扩股完成后,再由张克强等人控制的华美集团和华美丰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兴云信100%股权收购,从而占有盐湖集团股份。
根据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兴云信通过信托协议代华美系持有盐湖集团股份,随着盐湖集团的上市,兴云信大股东兴云投资以及华美方面都有意将兴云信的所有权完成变更。
审讯笔录显示,兴云投资总会计师杨承佳称,一旦兴云信代持的股份变现,将产生巨额税收,因兴云信的收入与巨额税收严重不符,大股东兴云投资无法接受这一局面。
而对于华美方面来说,自己的巨额出资挂靠在兴云信名下也不放心,因此意欲将兴云信的股权完全收购。
不过,公诉方在庭审时认为,在收购兴云信的过程中,华美方面参与了工商变更过程的造假。
审讯笔录显示,负责整个增资过程设计的华美丰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宋世新表示,“兴云投资唯一接受的方式,是我们按照8050万元的金额,收购兴云信全部股权。转让过程的手续办理由兴云投资操作,中介费用由华美方面承担。这笔中介费用在20万左右。”最后双方按照上述约定完成转让。
而交易另一方,兴云投资总经理董晓云在笔录中表示,在转让兴云信的过程中,他授意公司员工崔伟用造假的方法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造假工作层层外包
为何正常的工商变更要以造假的方式完成?
华美集团办公室主任田旭告诉记者,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兴云信的成立并不需要兴云投资的大股东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但由于是国企性质,一旦涉及转让,由于未在云南中烟备案,批复会遇到相当阻力,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然而,兴云信的出售对兴云投资来说,某种程度上却是迫在眉睫的操作。华美集团代理总裁陈金龙表示,当时兴云信在运营几年之后,亏空已达2000万元。这也是为何兴云信的资产评估值仅为6000万元左右,兴云投资却坚持以8050万元的价格出售的原因之一。“华美之所以也同意了这个转让价格,也是希望买个踏实,直到案发后,我们公司才知道转让手续涉嫌造假!”陈金龙透露。
而最终的造假程度,却超出了董晓云的意料。董晓云在笔录中表示,“我在媒体报道造假事件之后非常吃惊。之所以吃惊,并不是因为造假本身。而是因为变更手续中有几样材料,如转让协议等,公司本来就有,不必造假。没想到崔伟为了省事全部使用假材料,连我的签名也是假的”。
潮州人“老李”完成造假
作为整个工商变更手续的直接负责人,崔伟又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外包。他找到子公司兴云信办公室的员工李海涛,具体操作此事。审讯笔录信息显示,李海涛在工商局咨询了相关流程之后,被对方告知相关工商资料不齐全,未被受理。
此时,上层的催促让崔伟感到了压力,无奈之下,崔伟找到深圳某工商咨询代理公司的员工钟舸。
钟舸的审讯笔录显示,面对资料缺失,钟舸也感觉难以操作。由于兴云投资由数家股东参股,转让手续必须有上述股东方的同意。最终,钟舸选择了造假。钟舸表示,他找来一个叫“老李”的潮州人,老李按照他提供的兴云投资的公司章程,伪造兴云投资几家股东公司的公章。
另外,由于兴云信真实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标准,不符合变更的格式要求,“老李”又进行了“再创作”。钟舸在笔录中表示,整个工商变更造假过程,他直接与崔伟联系,从未与华美方面进行过接触。而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老李”的全名。
相关链接
2006年,盐湖集团增资扩股,兴云信以3.68亿元入股,持有其7.56%的股权。其中,该笔出资额中的绝大部分由华美方面承担。
2011年9月,昆明市检察院向昆明市中级法院对张克强等人提起公诉,指控其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冒用深圳兴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国企身份,参与盐湖集团增资扩股,从而占有盐湖集团股份。
案发后,一份由中国学术界著名刑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等五人签名的“云南张克强等人涉嫌诈骗罪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公开披露,五位法律专家结合刑事法理论,认为被告人张克强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此后,案件审理陷入僵局,虽然其后历经两次开庭,仍未有最终结果,张克强等人关押至今。
相关新闻
“国有资产流失”要有清晰界定
近日,盐湖股权案当事人华美集团原董事长张克强的儿子张远捷,公开发表了一篇声明,称自己父亲的投资行为,并未涉及诈骗国有资产。
抛开这起案件本身的是非不谈,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是造成诸多民营企业家在事业上陷入“滑铁卢”的首要原因,不少企业家因此身陷囹圄。
何为“流失”?按照字面含义解释,就是国有资产相对于过去某个特定时间点,出现了缩水现象。而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应该是确定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关键。
如果按照国有资产的最高值来作为评估起始点,那么,未来任何时间的商业行为,对国有资产的估值低于这个阶段性高点,必然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按照这一逻辑推演,如果国有资产在转让之后,大幅增值,国有资产也涉及流失。
不过,若国有资产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过户之后,其增值部分对国有资产的原持有人如果意味着国资流失的话,那么,假设交易之后资产价格下跌,是否国有资产的原持有人要赔偿损失?上述理论是否违反了“公平交易”这一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原则?
2009年9月10日,云南红塔集团将其持有的全部云南白药国有股6581万股转让给陈发树,每股转让价格33.54元,总价款为22.08亿元。转让之后,云南白药股价仍继续上涨。
2012年1月17日,中国烟草总公司回复称“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虽然在云南红塔与陈发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云南白药股价大幅上涨,但事实上,无论是陈发树,还是云南红塔,都不可能确定股权转让之后,云南白药股价的走势。而不可预测性,正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特性。
所以,交易双方签署的交易价格,已经包含了风险溢价。假设云南红塔集团和陈发树之间的交易无需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则一切都简单得多,只要交易达成,无论之后股价走势如何,双方都应愿赌服输。而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协议签订了两年多之后才下达批复,以签署转让协议之后股价继续上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否决交易,这对资产交易的另一方来说,欠缺公平。
而盐湖股权案最具争议的一点在于,盐湖集团的增资扩股项目在华美集团入股之前,已经被云南兴云投资的上级单位云南中烟,以“投资前景不明”为由否决,在华美系以信托形式,用兴云信的名义以自有资金入股之后形成的收益,很难说仍属云南中烟,而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全盘否定交易行为是否公允亦值得追问。
笔者认为,陈发树、张克强的投资行为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危及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应该有一个明确、公正的判决,以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