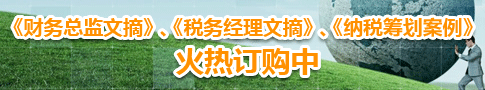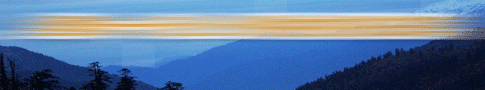| 2013年没有IPO的保荐人:突围、转型、反思 |
| 发布日期:2013/11/6 来源:上海证券报 编辑:Cherry 阅读次数:3367次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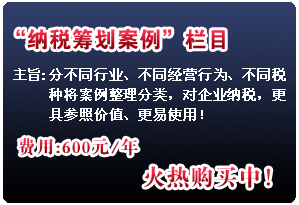
到今年11月2日,IPO暂停已整整一年。
相关统计显示,2012年,共有154只新股首发上市,券商揽获保荐承销费用合计55.7亿元,较2011年同期的132.3亿元规模回落近6成。但
2013年以来,券商IPO业务更是零收入。
与此同时,监管层空前严厉的财务核查,致使约280家IPO企业知难而退,个别企业的造假行径被曝光,公司及中介方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个别券商的IPO项目被暂缓受理。
在2013年没有IPO的日子里,曾经被券商高度倚重的核心团队——投行部的保荐人群体,不得不面对降薪的现实,开始体味从未有过的严冬滋味。
在这一年里,他们开始有时间,在质疑与困境中反思与转型。
或许,这原本就是一个被误读的职业。他们中多数勤勉而低调,甚至自嘲为过度出差、趴快印店、一天见7家客户的金融民工;他们从底层攀爬到独当一面,经历着常人无法知晓的苦楚;在没有IPO的当下,他们忍不住在微博上相互调侃与吐槽。
面对严冬,不少专做IPO的保荐人开始转型,转做并购等提前业务,但介入较浅。“其实,企业希望是一位导演而不仅是演员来协调兼并重组或上市的整个进程。”中德证券保荐人张国峰说,“一流的服务是导演,二流的服务是演员”。
“更深层次的是利益分配机制问题。”某资深保荐人说,签字保荐人非项目负责人,导致利益与风险分离,这是引发投行IPO困境、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大家更看重短期利益,很少有人考虑长远问题。”
保荐人过冬 这个冬天怎么过?
变革风,越刮越猛;监管层,严上加严;IPO开闸又好像春天般可望不可及。
冷!本土投行业对“冬”的感受,第一次这么剧烈;保荐人对高处不胜寒的体悟,第一次这么真实。
他们被视为本土投行里的精英,至今总人数不过三千,从生活状态到心路历程,一向鲜为人知。
对照华尔街,国内媒体对这群人的描绘往往偏花边:年薪百万以上,出入都是公务舱,五星级酒店,与上市公司董事长们称兄道弟,幕后出谋划策……
这样的剧情也许太“高于生活”了。
大部分保荐人对自己的定义是:金融民工——事业感缺失、薪酬不稳定、没有生活、常年亚健康,满腹委屈无处诉只好揶揄自嘲。
而逢此转型之冬,思考的意义远远大于自怨自艾。
越来越多的保荐人在惴惴不安、迷茫踯躅中反思与求变,在最寒冷的时候“围炉”夜话:关于IPO困境、关于保代制、关于造假、关于并购、关于转型、关于写书、关于离开……
越冬的故事谁都会有,因为冬天的到来,正是一个人反思的契机,一个行业苏醒的前奏。
整 整一年。
继去年11月2日浙江世宝登陆中小板之后,新股发行停摆至今……
荣呆会:我们“会里”故事多
天冷了,就想找个地方取暖。荣呆会,成为今年投行业越冬时节一抹难得的亮色。
一群素日混战江湖的对手们,放下刀枪,共建以文会友、交流心得的精神茶社。
创始人阿土哥,是个容易被当成八零后的激情文雅中年男,突发奇想邀约了饭局,应者云集,于是有了这个同业盛会。
所谓“荣呆”,业内人一看便知:指在“著名”的荣大打印店“呆过”的A股投行人。
当前成员已逾90人,来自超过30家券商,多数拥有保荐代表人资格,平均从业6.8年以上。
他们当中,有上世纪90年代出道的老投行,有2004年首批注册的保代,业界诸多微博达人亦悉数入会。
荣呆会很有趣。
入会申请须经管委会审议通过(管委会与发审委同样采用7人投票须5票同意的议事规则)。荣呆会和荣呆会管委会简称“会里”,资本市场人士无不感受到其中满溢的揶揄、自嘲趣味。
荣呆会很有用。
几个男多女少的微信吐槽群,应着“越冬”的景,很有点同命相依、抱团取暖的意思。但别忘记,他们可是精明过人的资本商人,诗文唱和、吐槽抱怨、八卦往来之间,多少业务信息与合作意愿也暗通款曲、互相试探。
IPO鼎盛时,大家还是互掐的对手,这种跨公司、民间互助式的合作雏形好像没太多价值,但面对金融全产业链竞争的未来,这种合作便彰显其意义。
荣呆会很真实。
透过这样一个组织,投行人当下最真实、草根的一面尽显。
例如,无可奈何的投行产能过剩、感觉鸡肋的IPO剩筵、寄予厚望的各类非IPO业务……这些是保荐人们的共同关键词。
又如,面对西式投行的比较标杆,国内企业无底线的道德黑洞,利益错综复杂的新股发行环境,监管层“指定”承担的核查责任……这些是保荐人们的共通焦虑。
多少压力、彷徨与无奈。不少资深保荐人诚心学佛,寻一方精神家园;也有一部分保荐人随着休息时间大幅增加,制定了周密的锻炼计划——美国特种部队教官撰写的《无器械健身》正在圈内流行。
更多时候,子夜时分微信群里忽然掀起一个或多个话题高潮,令平时太过忙碌的保荐人集体停顿。
就像子夜里的星,虽然带不来光明,却能带来希望。
保荐人集体谋创新:说到底还是“回归”
保荐制推行十年,保荐人仍是小众。
从底层攀爬、到苦熬考试、再到独当一面,一名保荐人自身的打拼不在话下,如今行业冬寒,什么转型、创新、回归,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荣呆会的保荐人群友们,基本是各券商中层往上,每谈及此,往往始而慷慨激昂,末了却唉声叹气。
眼下,IPO停摆,并购项目成投行业务主流。公司债、私募债、股权质押、ABS(资产支撑证券化)、类信托产品等,统统成为被竞夺的猎物。
看上去不愁温饱,可目前投行介入资金业务的手段还显生硬,多数靠打手续费和通道费的价格战,没太多体现投行人擅长的交易架构设计。
另外,业务结构的变化,必然引发组织模式的改变。本轮IPO暂停及空前的财务核查,导致众多IPO项目的操作周期大大拖长,结果难以预料。
于是乎,众多以“低工资高提成、小团队全业务链条”为特征的投行小团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投入不断,收益不见。
还没等到IPO开闸,不创新,不转型的队伍估计就要饿死在路上了。
来自中德证券的保荐人张国峰,感受颇深——“多层级、专业化,曾经是大投行的专利,如今中小投行纷纷跟上脚步。”
“一流的服务是导演,二流的服务是演员”,张国峰说:企业希望是一位导演而不仅是演员来协调兼并重组,或者上市的进程。
而要想成为导演,没有对行业、对业内上下游企业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的。
“今天做化工、明天做医药,到最后企业都对你半信半疑。”现在,张国峰自己就专注于软件和电子信息行业的项目。
但也有另一种声音。
“有的公司现在完全要求投行团队大包干,公司只收取牌照费,这一做法不会持久。”
还有过来人警示:投行按照业务流程进行专业分工,确实有利于提高效率,但若做得不好,也会有内部扯皮的问题。
例如,大投行模式做得最好的某投行,2011年—2012年接连有项目被毙,远远多于前几年被否项目数量之和。据透露,这也与客户开发与项目执行的分离有关系。
当然,资本市场业务由专门的人来负责,这绝对有必要。但客户开发与项目执行是否绝对分离,各家还要视自身情况来处理。
其实不妨看看我国香港市场,投行的专业定位很明确。能做承销业务的,就那么一些大行,不会太多。很多中小投行,不会去抢承销业务,而是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比如保荐、并购、持续督导。 “国内投行一般什么都做,没有差异化服务。”荣呆会的多位保荐人都这样告诉记者。
在他们眼里,IPO和再融资等保荐类业务,本来只是投行可做业务的一部分,但2007年到2011年间,这类业务极其火爆,回报率很高,几乎所有券商都在扩大保荐业务的产能,最终风险暴露。
到现在,很多投行又一窝蜂去经营债券、并购、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只为在IPO停发时找些收入覆盖成本,目的是解决人员温饱问题,而并非以此为长期目标。
如此“创新”虽然也是“新”,试问如何形成核心竞争力?
“演员”也好,“导演”也罢,投行业十年一觉,所谓转型,创新,更多意义上只是回归真正的投行。
对那些只关心保荐业务的投行人来说,这个冬天倒真的算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转折点。
案中人反思造假案:扭曲的利益机制
说到保荐人,绕不开的话题是造假。可如果一刀切将他们抨击为资本市场乱象的始作俑者,实在有转嫁之嫌。
晓程君,一家中游券商投行部负责人。三年一线项目经验,加之三年团队管理经验,更重要的,他是某个“知名”造假案例IPO的直接负责人。
“签字保荐人非项目负责人,导致利益与风险分离,这是引发投行IPO困境、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在晓程君看来,出问题的投行,不能不说有管理上的原因,例如,个别券商的项目,签、做分离,责、利不对等。
此前,保荐制规定一个保荐人只能同时签一个项目,这条政策原意是想让保荐代表人更负责对待每个项目,同时可在总量上控制项目数量。
但从保荐机构的角度看,如此规定导致机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而加快保荐代表人周转速度成了提高机构业绩的重要手段。
再从保荐人的角度出发,因为项目周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很难做到前后项目在时间上的完美衔接。
“如果前一个项目没发行出来时,手头做的项目恰好需要签字,自己就没法签,只能找其他保代签字;等自己签字的前一个项目发行后,手头的其他项目很可能达不到上报条件,为了不浪费签字权,也只能去签其他人做的项目。”
晓程君说,久而久之,很多项目出现了签字人与项目负责人的分离,签字人在证监会审核前突击看看材料,也能做到对项目比较熟悉,但是有没有时间做更深度的思考,就难说了。
还有奖金分配方面,项目奖金是向项目组而不是签字人倾斜的。签字人拿签字费,承担保荐风险,但项目奖金却不多;而项目组分享大部分项目奖金,却不用承担保荐风险。
在这种机制下,不同投行人员的利益与责任完全不对等,项目风险大幅增加。
随着绿大地、胜景山河等恶性造假案迭发,IPO造假几乎被视作行业性的丑闻。
而对晓程君这样,身处漩涡的保荐人群体,既有被倾听和理解的渴望,亦有太多百口莫辩的无奈。
沈明清是保荐人阶层中的新手,获得保荐人身份不过两年,但刻苦努力,为人机敏“会来事儿”,他对人情世故的判断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明镜儿式的”,颇受领导与客户偏爱,成长很快。
在一次吐槽饭局上,沈明清也说了自己对造假的看法:“保荐机构与保荐人话语权不对等,是我们作为风险把关第一责任人失效的重要原因。”
“保荐人签字要承担保荐风险,按说签字会非常谨慎,但保荐人很难对抗公司说不签项目,有些项目是怀疑有问题,但要拿到证据证实是很困难的。承接项目的时候,也知道有些企业是有问题的,但保荐机构或者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接,接了的项目又很难顶住各方压力不上报。”
精明的沈明清也有点无奈,“IPO好的时候不愁项目来源,但真正做到能够挑项目还是不易的,机构和保荐人都是如此。”
过来人从业甘苦谈:战胜心魔 常踩刹车
房叔40开外,是首批保荐人,如今在投行圈已属“高龄”。
之所以闻名,缘于他疯狂买房的举动。据说,每收到一笔项目奖金,房叔就买套房产,至今资产难以估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但据说房叔从业这么久,还真没发现哪个丑闻牵连到他。
如何做到守身如玉,房叔常自嘲:“短期暴富是人性中的魔鬼,国内资本圈尤其如此。我要活得久,才能住我那些房子啊。”
是自嘲,却也道出过来人的从业经验与领悟。
国内很多投行都采用小团队包干制,个人收益与绩效紧密挂钩,IPO火爆时,项目很多,一个人同时忙几个项目很常见,项目出来就有奖金拿。
原本投行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在每年都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完成项目是成员们考虑的重点。
由此造成的现实是,保荐人对企业提供的材料缺少进一步的验证,对某些风险考虑不周,底稿只满足申报材料的基本要求,待申报后再按要求补齐,是常见的操作方式。
在绩效激励下向前冲,只踩油门不踩刹车,项目出风险是早晚的事。
上周,证监会披露对IPO企业天能科技及相关中介的处罚决定。调查人员有段话饶有意味:若中介机构不能客观独立、勤勉尽责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过程就是“复印机”,看似材料很充分,形式很完美,作用其实不大。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圈子里常常流传一些“牛”案例,提醒着市场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规则:某券商保荐人发现存在造假,其后该项目被另一券商承接,最后成功上市。
“这个市场至今仍然膜拜类似的情况。”
见多识广的房叔最有感触:“我曾拒绝掉三个项目,最后都顺利过会,别人以此为荣,到处招摇,而我接触的几个企业都对我变得怀疑谨慎。”
“过客”心得
保荐人群体流动性很高,干个三、五年跳槽的不在少数,干了N年没跳槽的罕见,十年以上在一家公司的更是凤毛麟角。
人各有志,许多中途离开的过客亦各有心得。
一转眼,昭明来上海已整七年。从投行小兵走到投行中层,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的扩容潮,投行兴衰更替,保荐人一字千金。
昭明见证了少数人得意洋洋大发横财,更看到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同行苦逼着兜售青春。这让他心有余悸。
终于,昭明厌倦了:“为什么会计师、律师都有终生职业,而保荐人则总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稳定,都想着捞一票就走。”
现在,他和朋友开了一家很小的投资公司。“如果我真的有找到好公司的眼光,可以卖给资本市场。那为何我自己不买?”
“做投行时,我觉得自己很浮躁,赚钱找不到逻辑。看到市场永远在批判发行审核体制,但什么是正确的?我阅读大量公司法和证券法方面的教材,几乎搜罗了国内所有可见的专著,同时搜集了美国一线法学院的主流教材专著和经典论文。对着这个问题,结论永远是争论。”
有意思的是,高西庆曾于1996年10月著文《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沈朝辉也写过《流行的误解——注册制和审核制》。但20年过去,资本市场仍没能够在“实质性审核”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做出自己的抉择。
“百乐门小艳红”也是从投行业半途离开者之一。她早年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后供职于PE,继而去了香港,后赴英国。虽然离开的时候,有些人说,她考试没过;但小艳红却问:我们考试为的是什么?
小艳红写的不少散文、游学记录和对投行的分析,深刻精彩。“一度,我曾想和她一样。不过她是南渡,我则选择了北归。”昭明说。
就在10月底,小艳红出了本书,名为《亲历投行——中国投行的若干传言与真相》,无意间奠定她投行圈知性美女的地位。
小艳红说:“2013年夏天,在书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发现事实上仍然有很多人对中国的投行业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很多人更喜欢以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别人在做什么。在香港和伦敦求学期间,一些我新结识的朋友在不经意的聊天中提及了一些对中国投行的误解。听说我在投行工作,一个在商业银行做投行业务的人说:那你成天都与合同打交道吧。一个在国际大投行做sales的人问我:那你平时买什么股票?一个在伦敦做外汇业务的人听说我在国内投行负责过中后台业务说:那你主要是做行政工作的吧。”
小艳红的书一经出版,马上风靡了保荐人圈子,并逐步向监管部门里的“哥们儿、姐们儿”扩散。
帮小艳红的书写序的是前述荣呆会的创始人——阿土哥。“他很仗义地说,等书出了他要先买几十本,预备送给在他团队里实习的大学生和新人。一想到他们的办公室可能各处散落着有我照片的书,我偷偷地在心里笑了。”小艳红说。
|
|
|
|